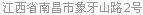|
陶寺文化 第二章 遗址文化——龙乡陶寺帝尧都 四、蟠龙陶盘,图腾崇拜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这句话在中国可谓是人人皆知的事实,龙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图腾”即为“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标志。”图腾文化作为古老的民俗文化,是上古时期氏族社会对于本族由来、氏族标志的原始崇拜。伏羲龙身、女娲蛇身,均为龙图腾,上古帝王黄帝、尧、舜、禹也为龙图腾,这些古老的祖先,都被看作是龙图腾。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对龙的崇拜从氏族部落的图腾演变为王权的象征,更具神秘色彩。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龙是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凝聚力的来源,龙图腾不仅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起到重要的影响,在当下社会也占据着重要位置,总之,龙图腾在中国贯穿古今的文化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年陶寺遗址大型墓中出土了彩绘蟠龙的陶盘,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有关龙图案的最早标本,对于研究龙图腾崇拜的起源和陶寺遗址的文化属性具有重要的价值。蟠龙纹陶盘为泥制褐陶,或黑陶衣,盘壁斜收成平底,内壁磨光,以彩或红、白彩绘出蟠龙图案。蟠龙陶盘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盘底彩绘龙纹为一条卷曲身、双行麟甲、有鳍、张口露齿、口衔羽毛的龙,图案整体线条匀称、风格古朴、神态生动。《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陶盘上的蟠龙图案做了详细的描述: “龙纹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盘曲状,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中心。与商周蟠龙纹铜盘的龙纹比较,构图略有不同,后者是头在盘底中心,身向外卷,尾在最外圈,在表现手法上更接近蛇类的自然习性。从陶寺蟠龙的具体形象看,作蛇躯麟身,方头,豆状圆目,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杈状分支,有的在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鬣状物,与商周蟠龙的明显区别是无角,也无爪。这同其盘曲的形态一样,也是陶寺龙纹具有一定原始性的反映。从身、尾、目的形状和它口吐长信的特征看,很像蛇,但从方头、巨口、露齿看,又与鳄鱼接近。从而可以看出,陶寺蟠龙的模样儿,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综合体。” 还有学者认为陶盘的蟠龙图案是以蛇为主体,综合了鳄、羊、鸟等动物的部分特征组成的复合图腾,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的共同族徽,也是祭器和神权的象征。 陶寺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即是龙图腾崇拜的表现,这与帝尧时期崇拜赤龙图腾是一致的。相传尧的母亲庆都和赤龙相交生下帝尧,尧部落崇拜赤龙,赤龙也成为陶唐氏图腾的象征。关于尧的出生,文献多有记载: 《太平预览》引《春秋合诚图》:“帝尧之母曰庆都,生而神异,常有黄云覆上。”罗泌《路史》也有记载:“帝尧陶唐氏,姬姓,高辛氏第二子也。母陈丰氏,曰庆都,尝观三河之首,赤帝显图,奄然风雨。庆都遇而萌之,黄云覆之,震,十有四月而生于丹陵,曰尧,是曰放勋。” 《汉碑·成阳灵台碑》记载:“唯帝尧母,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如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 《潜夫论·五德志》记载:“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号唐。” 《竹本纪年》记载:“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赤)受天祐。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 从庆都感应生尧的记载可清晰地看出,上古神话中始祖诞生源于感应生子,这也是上古社会图腾崇拜观念的表现。在我国庞大的神话体系中,这类神话比较常见,如“女狄吞月精而生禹”女狄吃下月的精华而生出禹;炎帝降生是其母任姒“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上古时期氏族首领的诞生无疑不是充满神奇色彩,这些始祖祖先也不无带有“神格”。在后世君主中,他们的出生也多蒙上一层神秘的感生神话面纱,且帝王往往被视为龙,“真龙天子”“龙种”“龙颜”“龙体”等一切都与龙有关,这既是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又是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 回归帝尧的诞生,上述记载不免有将帝尧神化的成分,认为他是由赤龙或河龙所生,但从另一个方面不难看出,帝尧时期确有将龙视为图腾的痕迹。在陶寺四座大型墓中出土的彩绘木盘,内壁磨光,以红彩和白彩绘成的蟠龙,同样形为方头、巨口、圆目、长舌外伸、无角、巨爪,是我国最早见到的龙形象之一,这为研究我国龙图腾崇拜的起源提供了较为原始的凭证,对于探讨陶寺遗址的文化属性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扁壶朱书,人文教化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开始,是文治教化的重要工具,它打破了口语传承的时空局限,使文明能够以符号的形式得以传承。文字历经从象形图画到成熟的文化体系的发展过程,通常认为人类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证明,商代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残破的陶制扁壶,年出土于陶寺遗址灰坑H,距今约余年。该器皿乍一看和普通生活用具并无区别,但是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同时发现了朱书符号,这赋予这个看似普通的扁壶极大的价值。在扁壶鼓腹面凸起的一侧,用朱笔写有一“文”字。殷墟甲骨卜辞中就出现“文”字,陶寺出土的扁壶朱书上的“文”字字形和甲骨文上的“文”字极为相似,这足以说明早在商代甲骨文之前,就产生了初始阶段的文字符号,由此证明文字有着更久远的发展史。扁壶另一侧也有用朱笔写的字,多被解释为“易”字或“尧”字,考古专家根据陶寺遗址周围所处的环境,更倾向于此字是“尧”字的说法。因为陶寺城址是处在黄土塬上有着高大城垣的城邑,这与《说文》中的“尧”的本意接近。也有学者认为扁壶上的“文”与“尧”是尧后人追忆先祖的称谓,是对帝尧丰功伟绩的记录。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朱书文字,因在陶上,也被称为“陶文”。 结合年前帝尧时期的历史背景,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就有了极大的文化内涵,加之陶寺城址和古观象台的发掘,表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已有较高的水平,为文字的产生奠定了丰硕的物质和文化基础。陶寺朱书文字的发现,为中国文字发展史涂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陶寺遗址文化中彰显人文礼制的除了朱书文字、观象台、蟠龙纹陶盘外,还有铜铃、乐器等文物,可看作当时社会政治、礼制文化的真实反映。观象台用于观天授时和祭祀神灵,可说明当时已有历法和节令来指导农业生产,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陶盘上的蟠龙纹既是图腾崇拜的表现,也代表了帝尧的身份,更为中华民族作为“龙的传人”的说法增添实证;陶寺还出土有铜铃,铜铃在古代一般在宣布政教法令和战争时使用,大多悬挂于高处位置;陶寺遗址出土的代表性乐器“特磬”和“鼍鼓”,是当时的重要礼乐器,经测试,特磬可以敲出六个音色,说明帝尧时期“韶乐”是存在的,可视为“国乐”的一种,这表明当时已有一定的礼乐仪式和制度存在,可见当时的陶寺已经是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氏族部落。 墓葬文化同样也是古代礼仪文化的一种。在陶寺出土占地近三万平方米的大型墓葬群,墓葬约有一千余座。墓葬规格严密,有大型王墓、中型墓、小型墓等,由墓葬规格和随葬物品可看出墓主的不同身份,进一步可看出社会结构的变化程度,已出现官职大小、贫富差异的现象,有说法认为从墓葬规格可看出当时已经出现阶级分化,人类社会进入新的阶段。 陶寺遗址文化同样反映出古时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可作为仪礼文化的一种表现。在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器具,既有生产生活的实用器具,也有绘有装饰的礼仪器具,可以看出文化艺术和审美情趣已经渗透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如彩绘云雷纹陶壶,用红、白、黑绘出云雷纹,壶颈下一圈绘有红色条带,陶壶整体规整,纹饰美观,是礼仪器具的一种。再如彩绘木器、陶器,木制器具包括鼓、盘、豆、斗、匣等各式各样的器具,既有单色的图案,也有白、红、黄、黑、蓝等多色图案。彩绘陶器有壶、盘、盆、罐、豆等器具,多为礼制用具。通常绘有红、黄、白、蓝等色,纹饰更是多样,有圈点纹、条带纹、几何纹、云雷纹、龙纹等,图案较抽象,多种纹样勾连,十分精美。整体来看陶寺出土的器具,其中既有造型美观的盛物器具,如圆足罐、瓮、缸、盆等,也有厚重庄严的礼制用具,种类繁多、造型各异。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对文化、生活、大自然的理解与表达,并且表明他们有了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识。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陶寺遗址文化的种种表现,把中国的礼仪制度提前到帝尧时期,无论是文字、历法、礼仪器具等,其中都蕴含着文明的内涵,文明与礼仪在年前的陶寺就已出现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所有这一切更进一步为尧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实证,再结合平阳大地上流传的众多帝尧传说:尧都平阳、尧制农历、诽谤木、帝尧访贤、帝尧嫁女等,可以看出尧文化在晋南地区的传承与发展。作为陶寺文化时期古平阳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尧也因其功绩被后世称为民师典范、文明始祖。 六、陶之文明,龙乡帝都 历来学者对帝尧文化的研究多从考古发掘、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等方面展开,这几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印证。相比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考古发掘更具说服性和实证性。陶寺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史书所记载的帝尧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风貌,也使口耳相传的有关帝尧的神话传说更加具有地域代表性,证实了陶寺是帝尧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帝尧之都”,陶寺遗址文化即代表了帝尧文明。 陶寺遗址文化表明帝尧时期的社会形成了一定的价值体系,为人文教化、社会稳定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充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本奠定了华夏民族的价值认知体系。出土的众多文物彰显出帝尧时期的礼仪制度和文明进程,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反映。遗址中的墓葬规格和随葬品显示出帝尧时期礼仪制度的完善,随后更进一步规范化,也就有了祭祀天地山川、祖先、图腾、殡葬仪礼和君臣之礼等众多礼法。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真实地还原了帝尧时期“敬授民时”的情景,也让人们看到祭祀神灵的实证。观象台可观象可祭天,具有民神杂糅的性质,在传播农事历法的同时,也凝聚了民心,同样是帝尧文明的重要组成要素。墓葬出土的众多器乐无不是陶寺帝尧礼仪文明的重要表现,古人常讲“礼乐崩坏”“礼修乐举”,意在说明在古代器乐的重要性。陶寺出土的众多器乐作为当时重要的礼乐器,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表征。 研究陶寺文化的众多论著中,认为陶寺文化是帝尧文化的占大多数。有人将陶寺遗址文化总结为“三个根”,首先是“中国之根”,陶寺古城址证明帝尧建都陶寺,而陶寺地区处于黄河中游,故“中国”之根在陶寺;二是华夏龙祖之根,陶寺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是帝尧时期龙图腾崇拜的表现,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龙文化”即从尧始;三是我国农业文明之根,陶寺古观象台即是最有力的佐证,帝尧派羲和分赴四方观测天象,制定出“四时闰历”,敬授民时,教民稼穑,农业文明始于帝尧时期。由此可见,陶寺遗址文化确立了陶寺帝尧文化的地位,最早中国从这里开始。陶寺遗址文化中所包含的礼仪、制度、信仰、道德等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核,帝尧文化被考古发掘、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等的多重证据印证,被越来越多地加以弘扬,帝尧文化因此成为我国优秀文化的源头之一。 百家号总指导:高忠严 内容顾问: 石国伟牛刚花 吕树明武红霞 百家号主编:陆瑶 图文编辑:穆晓瑜 |